性和身体虐待
岳海 心理治疗师

乱伦作为 创伤 近期获得了很多关注, 精神分析 对其受害者的研究阐明了一个内化的、被恨控制的 客体关系 的基本动力。在探索这些心理动力中我们必须记住:性兴奋时的施虐受虐部分让爱在性中补偿了恨。但当一个性反应被愤怒和恨淹没时,这会转化为性施虐受虐,在其中爱被用于服务攻击。性交会成为一种施虐受虐倾向的象征性满足,在性领域中复制我之前描述的在被恨所控制的关系中的互动。
不是所有的性虐待都被体验为攻击;由突破 俄狄浦斯 屏障所导致的 潜意识 的 婴儿 化性欲、性兴奋、满足和胜利等,和这样的胜利导致的内疚,复杂化了性虐待中的心理影响。然而当代际间(尤其是父母与 儿童 间)的乱伦出现时,引发的超我扭曲会破坏施虐父母影像整合进超我。性兴奋和内疚的冲突因此转变成脆弱的理想化和淹没性攻击相结合的超我,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创伤情景,在其中力比多和攻击性不再被区分。潜意识中对施害者和受害者的认同会变得混淆。强迫性重复地将他们后来的性生活转变成一连串创伤癖体验的乱伦受害者,经常难以区分他们究竟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
在临床情景中,这样的乱伦受害者再次激活了对受害 - 施害配对的认同,潜意识地试图再次创造创伤情景来消除它,恢复迫害者背后的理想化客体。另外,强迫性重复表达了想要报复,合理化对诱惑者的恨,以诱惑引诱者的形式潜在地将恨性欲化。对有与之前的治疗师有性经历的乱伦受害者的动力学治疗中有时候异常清晰地重复了这些体验。潜意识嫉妒当下的治疗师(不包括卷入混乱的恨和性欲混合,在其中患者体验自己为无助地陷入泥潭)是另一种负性治疗反应的来源。
最近的研究确认了性虐待历史在边缘 人格 障碍以及他们倾向于解离反应的重要性。 Paris 也指出,解离反应倾向并不就是性创伤的次发反应。在临床实践中,两种问题类型经常会一起看到。一些边缘患者呈现健忘、人格解体状态、甚至多重人格等形式的解离反应,患者能在认知上对此有觉察,但 情感 上是分裂的。
在这些解离反应中经常令人惊讶的是患者对一些看起来戏剧性的心理现象明显地漠不关心:实际上,一些患者表现出一种几乎藐视性的断言,认为他们的人格分裂是自动性的,拒绝认为需要为这现象负任何个人责任。经常,交替人格的解离会引起疑问:为什么一些看上去不协调的人格状态会相互之间处在分离状态。
在我的经验中,当治疗师询问患者的中心人格、她的意识、担心和责任等与这些分离的人格状态是怎样的关系时,这会立即触发一个新的 移情 发展。很多患者对此提问会发展出一个偏执反应;这发 展成一种特殊的移情倾向,在其中治疗师表现为一个迫害者角色,相反于 来访者 生活中的其他人,包括其他治疗师,他们被理想化为有帮助的、宽容的、不会质疑的、赞赏的和支持的。患者交替的人格状态呈现更多这些分裂的客体表象的特殊意义,可以在移情中澄清这分裂状态的功能。简而言之,从一个假设的观察、中心、“绝对”的自体来面对患者,会阐明在移情中隐藏的分裂,可以探索分裂人格状态中的潜意识动力,而这动力之前被通常的表面上没缘由的激活所掩盖。
患者现在会被引诱谴责治疗师不相信他的多重人格的存在。治疗师关心和中立的态度逐步让来访者增加他的 自我 觉察功能,对患者的体验感兴趣,不质疑其真实性,但而不是之前的防御性否认担心和被称为盲目地解离状态的行动化。
在严重人格障碍身上,这个我呈现的方法将模糊的、经常表面上无情感的剧情转变成具体的客体关系,在其中强烈的愤怒和攻击会出现,并与其他理想化的客体关系保持分裂。一旦在移情中明显出现在分裂的原始客体关系背景下相互分裂的峰值 情绪 状态,对这些发展的解释性整合就能开始。
这个方法不同于某些治疗师:倾向于探索每部分解离的人格状态同时尊重它的分裂条件,绕过对这条件防御性的否认。我相信这样的方法会导致不必要的延长解离条件,并会加重它
当这样的解离反应出现在现实或想象的过去的乱伦或性虐待的背景中时,一个相似的、防御地否认对解离过程的本质有担心,会经常被观察到。这样一种发展明显反差于另外些情况,在其中那些在精神分析探索下被压抑的过去性虐待经历,包括乱伦,被揭露出来,导致一种创伤情绪反应,会可能影响几个月的治疗关系,然后逐步修通。在这后面的情况中,一种创伤后应激综合征会在治疗关系中浮现;患者表现出对自己巨大的担心,对于虐待者关系的强烈的矛盾感,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性方面存在矛盾心理。详细描述这样一种创伤 记忆 恢复明显不同于长期在现在的对自己的一般的性生活或所有代表同性别的性创伤代理人的关系中表达恨、厌恶和反感的背景中重复唤起过去创伤性性体验。
在这样的情况中,尤其当创伤的性记忆反复表现在解离的自我状态中时,也会有一种特征性的对解离过程缺乏担心、否认或戏剧性地漠不关心。患者会在与一个恨和害怕的性对象的挣扎中坚持将治疗师看做“目击者”或支持者。在移情中,治疗师会被认同为施虐客体或一个阴谋的帮助者(例如,“无辜受殃”的母亲,她以微妙或不微妙的方式保护一个乱伦的父亲)。
次,世界看起来被分裂为站在迫害客体一边的和支持患者想那客体复仇的。由于当下文化关注性虐待,患者的分裂的客体关系的世界会被合理化为一个符合习惯的意识形态,认可和保持自己的作为受害者的身份。
我发现问患者问以下问题是有帮助的:是什么让恨继续留在他的生活中以及在他当下的冲突中它的功能是什么?。当过去性虐待的事实不清晰时,甚至在患者的记忆中也不清晰时,患者依然会坚持要求治疗师确认他的怀疑。治疗师的态度——患者当下的经验才更真实,患者自己会最终能够澄清和获得对内在过去的理解和控制——经常导致在移情中同样强烈的怀疑和愤怒,就如在试图澄清患者的中心自我体验和一种解离状态的关系时。也就是说,患者会不能够忍受治疗师的关心但中立的位置,这个和高于一切地需要将世界分成联盟和敌人是不一致的。治疗师持续解释患者对保持这样的分裂关系的需要,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会最终对在移情中施害者和受害者关系的活化(并频繁地角色反转)有更多的关注。由此可以分析作为患者的潜意识认同施害者,就如同对受害者的认同,共同组成了主要动力,保持了特征性的、铆定的恨。
这样一种治疗方法的一个积极结果是逐步把患者的性生活从它的被未认识的、没有代谢的恨所渗透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在早年遭受性虐待的受害者对性欲的反感有很多根源:他们身体和心理边界的入侵被体验为一种暴力攻击;一个人从处在父母功能中到成一个性虐待者的转变被体验为一种施虐背叛,还有瓦解了早期建立的整合的原始超我。在偏执倾向中早期迫害超我的再次投射强化了一个性攻击的攻击性意义,削弱了建立任何信任关系的能力。
由于患者自己的性冲动在性诱惑和虐待的激活而产生的潜意识的内疚,会增加这种对所有性欲的反感,被诱惑再次投射这内疚感,因此再次强化了患者的偏执地对待性客体和压抑性愿望、幻想和体验。如果酷刑创伤受害者必须再次觉察他们自己的施虐倾向,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意识认同受害者和施害者,性虐待受害者也必须再次觉察他们的潜意识认同创伤经验中的自体和客体双方中的自己的性欲。如果这样的再次相遇没有完成治疗就无法完成。 Stoller(1985) 将色情性兴奋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早期感觉体验的和潜意识地认同一个攻击性客体的融合——也就是说,色情的多形态的倒错的施虐受虐的根源——是与这连接相关的。在某个时候,一个缓和的、可忍受的施虐受虐倾向可能重新翻译成一个色情幻想的语言,打通成人生殖器性欲的多形态倒错部分。


恋爱受挫,应该如何应对?


女子婚前体检查出一种病被相恋7年男友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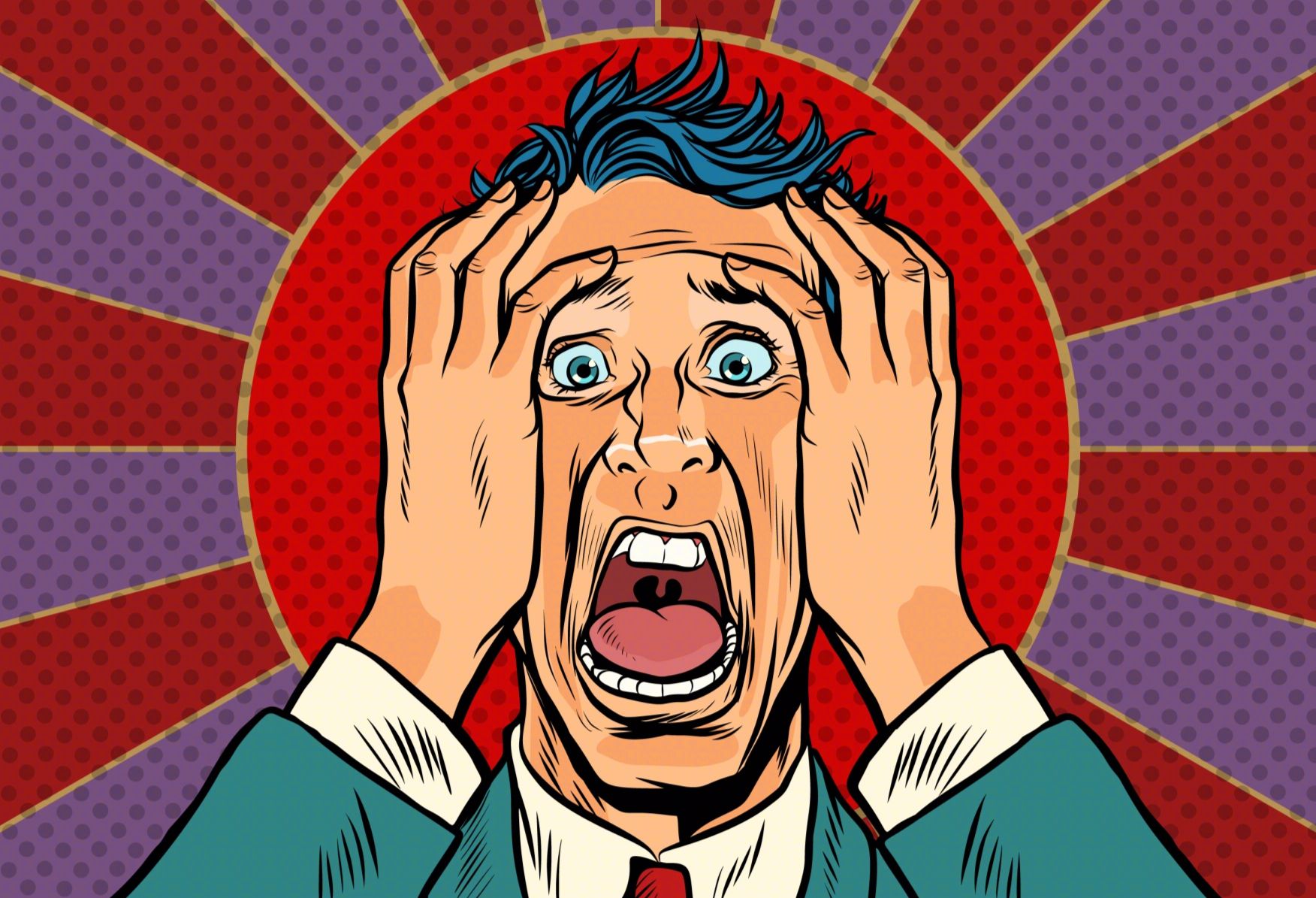
被害妄想症患者需要注意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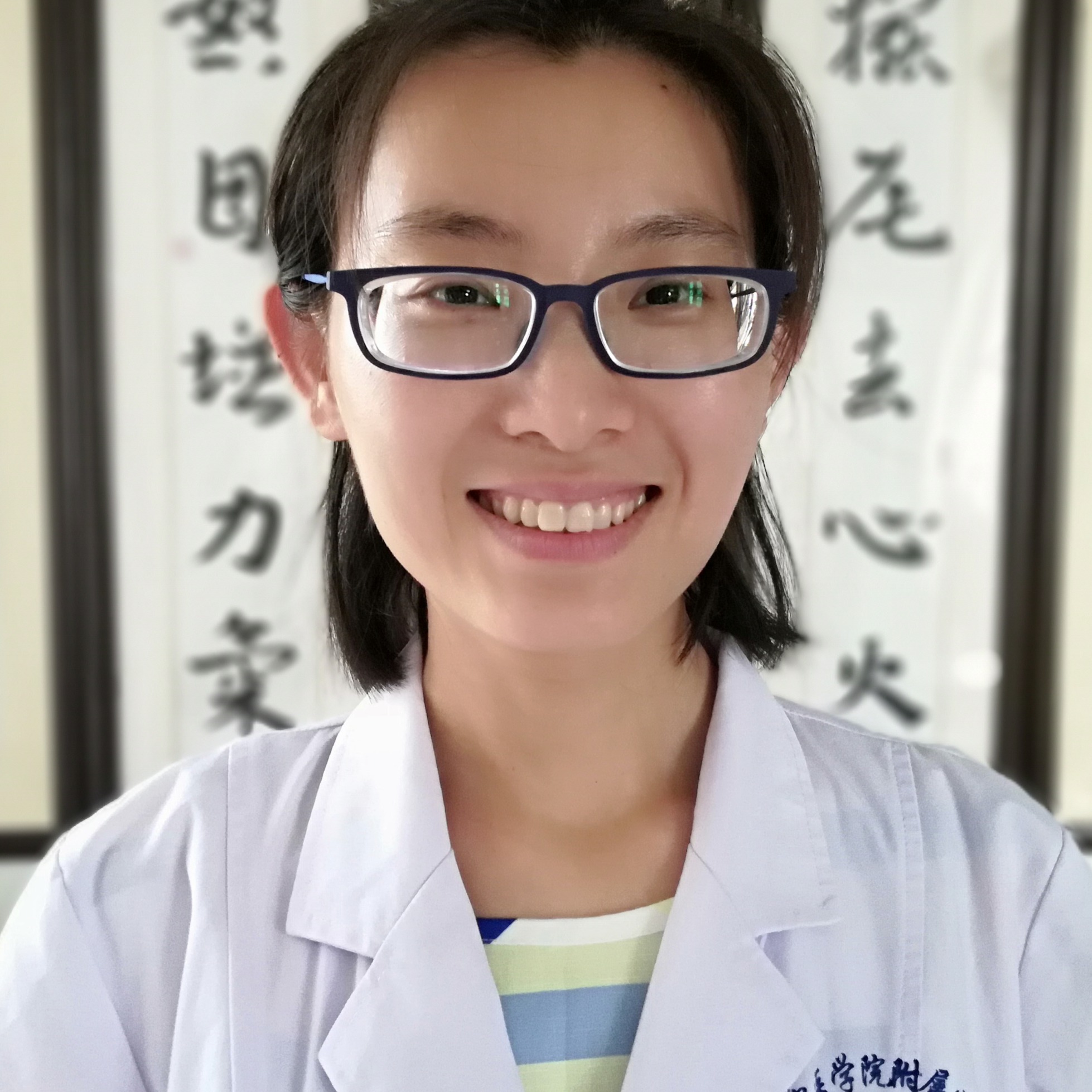

球类运动争议/直接攻击人体,难道不是合理霸凌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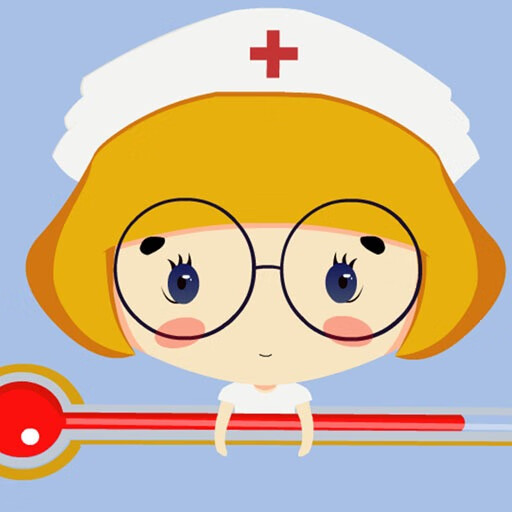

常接吻的人,身体不知不觉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家庭冷暴力比暴力更具杀伤力,等同于精神虐待


崩漏,女孩们的难言之隐


心率不齐原来也有性别歧视


性侵不会停止,我们只能教孩子怎么保护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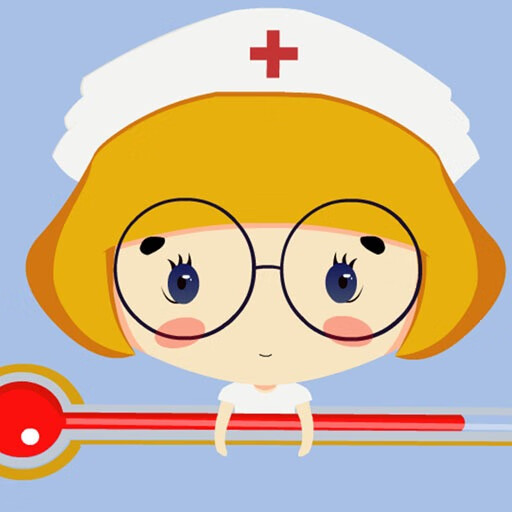

反家暴!可这种暴力我们一直都在遭受…


境界性人格分裂症:认知与情感的双重障碍

人格分裂与抑郁症的区分要点

强迫思维与人格分裂:两者关系及应对措施

男人喜欢骂老婆的心理原因及应对方法

多重人格分裂症的诊断与测试方法

人格分裂症:治疗方法与注意事项

人格分裂的识别与治疗

人格障碍类型及治疗方法概述

人格分裂的治疗方法

抑郁症与人格分裂的诊断要点
精神心理疾病咨询
17岁高中生抑郁症状咨询
精神问题咨询:情绪不稳定,人格分裂症疑似,如何改善
人格分裂症治疗与副人格消失问题咨询
校园暴力引发心理问题诊断
人格分裂与个体变化咨询
人格分裂与人际关系问题咨询
分裂样精神障碍的诊断与治疗
双重人格的诊断与治疗咨询
调整药物方案及头部疼痛诊断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