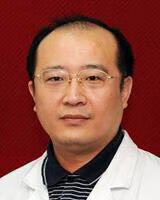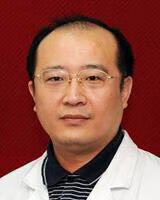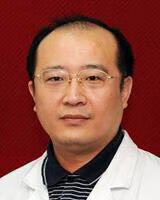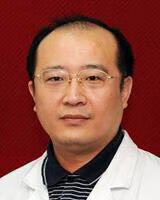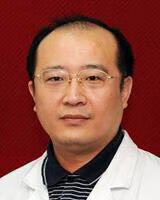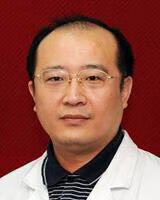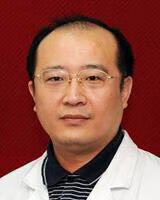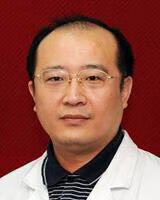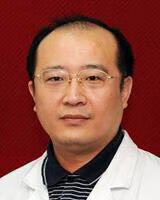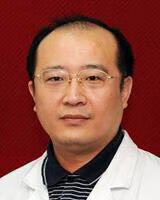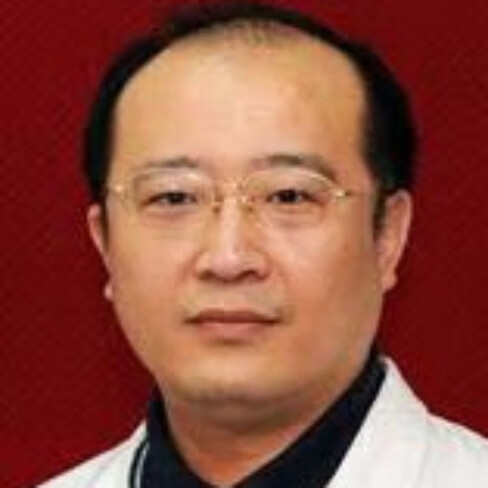文章
动脉血栓形成与静脉血栓形成之间的关联
动脉血栓形成与静脉血栓形成之间的关联 动脉血栓形成和静脉血栓栓塞(VTE)传统上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然而,与挑战这些区别的健康对照相比,无诱因的VTE患者发生亚临床和显性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更高。 肥胖可能解释动静脉疾病之间的关联:超重/肥胖患者易出现下肢静脉淤滞、慢性炎症、血脂异常、高血压和糖尿病;所有这些都会导致高凝状态、VTE和动脉粥样硬化。结合传统动脉疗法(抗血小板和他汀类药物)和静脉血栓形成疗法(抗凝剂)并将其重新应用于血管疾病患者的新型治疗方法正在出现。 传统上认为,动脉血栓形成和静脉血栓栓塞(VTE)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具有不同的病理生理学(动脉:血管壁病变和高剪切应力vs.静脉:淤滞和高凝状态)、不同的部位(动脉:冠状动脉和脑血管vs.静脉:下肢静脉和肺动脉)和不同的治疗(动脉:抗血小板药物和他汀类药物vs.静脉:抗凝剂)。 然而,动静脉血栓形成之间存在关联的假说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观察性研究提示外周动脉疾病、高脂血症、高血压与VTE之间存在关联时得到支持。虽然风险估值不一致,尤其是将体质指数(BMI)纳入多变量分析时,但许多学者随后研究了亚临床或临床动脉粥样硬化、动脉危险因素和VTE之间的关联。 关联的证据 相关性的流行病学: 2003年发表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299例未经选择的腿部深静脉血栓(DVT)患者和150名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对照受试者进行了颈动脉超声检查。 与有诱因的VTE患者和对照组相比,无诱因的VTE患者的颈动脉斑块患病率分别高2.3和1.8倍。随后的另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89例VTE患者(51.7%)的冠状动脉钙化发生率高于89例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对照组(28.1%)(p = 0.001)。在校正混杂因素(糖尿病、肥胖、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后,VTE和冠状动脉钙化之间的关联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综上所述,这些观察性研究强烈提示,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是VTE的独立危险因素(反之亦然)。 重要的是,一项基于丹麦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包括约25,000个DVT病例、约17,000个肺栓塞(PE)病例和约160,000个对照)证实了VTE与随后的临床动脉疾病相关: 在DVT或PE发生后的一年内,根据年龄、性别和指数日历年校正的心肌梗死或卒中相对危险度分别为1.88和2.73。在随后20年随访期间,VTE患者发生动脉事件的风险仍比无VTE的对照高20 ~ 40%。值得注意的是,在有诱因和无诱因的VTE患者中,动脉疾病的相对风险相似。 在另一个包含1919例VTE患者的队列中,中位随访48个月和51个月后观察到,15.1%的无诱因VTE患者和8.5%的有诱因VTE患者发生了至少1起有症状的动脉粥样硬化事件。校正年龄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其他危险因素后,无诱因VTE患者发生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是有诱因VTE患者的1.6倍(95% CI: 1.2 ~ 2.0)。 长期以来,心肌梗死和卒中一直被认为是后续VTE的潜在危险因素。两者均与后续VTE增加4倍相关。不活动在与卒中的关联中起主要作用: 无症状的深静脉血栓可在卒中患者的瘫痪肢体中发现,高达60%,而在非瘫痪肢体中为7%。有趣的是,有卒中或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的长期随访(即4 - 60个月,或 >60个月)显示,与无动脉疾病的对照组相比,VTE风险增加1.3倍。 VTE患者的心肌梗死或卒中风险高于对照 (反之亦然): 有症状或无症状卒中常与PE相关;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数据显示,在324例连续的PE患者中,通过头部MRI和神经科专家的体格检查进行系统评估,发现卵圆孔未闭与有症状卒中的风险增加6倍相关(9.5% vs. 1.5%)。 这一发现支持反常栓塞是合并卵圆孔未闭和PE患者发生缺血性卒中的重要机制的假设。其他疾病如血管炎、抗磷脂综合征或骨髓增殖性疾病表现为动脉和静脉血栓形成,但太罕见,无法解释这种相关性。 静脉和动脉血栓形成的共同危险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这种明显的关联。高龄是与VTE和动脉粥样硬化独立相关的最明显的危险因素。75岁以上人群的VTE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是20 ~ 39岁人群的15 ~ 20倍。 VTE的主要危险因素与动脉血栓形成是否存在相关性: 与动脉疾病和随后的VTE相似,VTE的遗传和获得性危险因素相互作用并导致随后的冠状动脉疾病或卒中。然而,这些关联尚未得到充分评估,原因可能是VTE危险因素与有症状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率略微增加相关。 几项观察性研究探讨了凝血因子V莱顿(factor V Leiden)、G20210A凝血酶原突变与冠心病之间的关联(杂合和纯合状态的汇总分析)。在一项荟萃分析中总结的数据表明,这些遗传倾向与VTE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关联较弱。在VTE前血栓形成基因突变和卒中之间也观察到正相关,但在冠心病方面,这些关联比在VTE方面弱。 激素治疗是年轻女性常见的危险因素。在发生VTE的年轻女性中,约有一半在发生VTE时服用基于雌激素的口服避孕药。暴露于雌激素类口服避孕药的妇女发生动脉事件的风险也增加了3倍。 这一相对风险与口服避孕药使用者的VTE相对风险相似,但动脉事件的绝对风险要低得多:例如,18 ~ 49岁女性人群的卒中发病率为18 / 10万人-年,而VTE发病率为77 / 10万人-年。在激素替代疗法(HRT)方面,HRT使用者的冠状动脉疾病和卒中风险略有增加,但该风险可能被低估,因为随机研究中仅纳入了低动脉风险的女性。 下肢骨科大手术与VTE密切相关,但应警惕合并的动脉血栓形成风险。在6,860例髋部骨折患者组成的前瞻性队列的数据中观察到,入院接受手术期间,卒中或心肌梗死的粗发生率为1.2%。 在另一项研究中,髋部骨折后的90日心肌梗死发生率为5% ~ 6%,而有症状的VTE发生于1%的患者。 最后,癌症是VTE的主要临床危险因素之一,也可能导致动脉血栓形成。在一项纳入1,469例癌症患者的队列研究中观察到动脉事件的2年累积发生率为2.8%。 与非癌症患者相比,动脉血栓形成的风险高出2倍。动脉事件的超额危险度似乎因癌症类型而异 (肺癌的超额危险度最大),与癌症分期相关,并且通常在诊断癌症后1年以上的生存期后消退。 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与VTE是否存在相关性: 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与VTE之间关联的临床证据仍不确定。脂质直接与凝血因子相互作用,而脂质颗粒可能提供启动凝血级联的表面。然而,一项荟萃分析及后续研究的数据总结显示,总胆固醇水平、HDL -胆固醇和VTE之间未观察到关联或不一致的关联。 LDL胆固醇水平较高与VTE风险增加2 ~ 4倍相关,但仅限于病例对照研究中的男性。在女性研究或队列研究中,高水平LDL胆固醇从未与VTE相关。除肥胖外,观察到的心血管疾病临床危险因素与VTE之间的关联较弱或不显著(高血压的OR 1.51 (95% CI, 1.23 ~ 1.85),糖尿病的OR 1.42 (95% CI, 1.12 ~ 1.77),吸烟的OR 1.18 (95% CI, 0.95 ~ 1.46))。 无诱因的VTE患者比有诱因的VTE患者更有可能携带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无诱因的VTE后动脉事件的发生率较高。 肥胖是否为动脉血栓形成和VTE之间关联的关键: 魏克氏三特征(Virchow‘s triad)的所有组成部分均可受到肥胖的影响,并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血栓形成: 淤滞: 肥胖患者长期腹内压升高,因此股总静脉血流速度降低,可能增加VTE的风险。 高凝状态: 肥胖导致慢性炎症状态,与纤维蛋白原、组织因子、因子VIII水平升高和纤溶潜能降低相关;体重减轻后,这种促血栓形成状态在生物学上被逆转。 血管病变:肥胖与血脂异常、高血压、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相关,这些都会导致血管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 探讨心血管危险因素与VTE之间关联的流行病学研究和荟萃分析的一个主要局限性是:未对几个重要混杂因素进行校正,尤其是肥胖。将肥胖确定为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和VTE之间关联的核心角色的第一步来自两项观察性研究,这些研究提示,观察到的胰岛素抵抗和VTE之间的关联并不独立于BMI。 最近的一项个体患者数据荟萃分析(IPDMA)表明,可改变的传统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即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和吸烟)与VTE总体或VTE亚型无关。 IPDMA汇总了9项前瞻性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测量了基线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和随后经过验证的VTE事件。这些研究包括244,865名参与者,每项研究在平均4.7 ~ 19.7年随访期间发生了4,910起VTE事件。在未校正的模型中,除当前吸烟外,所有心血管危险因素均与VTE明显正相关。 然而,对年龄、性别和BMI进行校正后,VTE与高血压 (风险比: 0.98; 95% CI: 0.89 ~ 1.07)、高脂血症 (HR = 0.97; 95% CI: 0.88 ~ 1.08)、糖尿病 (HR: 1.01; 95% CI: 0.89 ~ 1.15)、既往吸烟 (HR: 0.99; 95% CI: 0.93 ~ 1.06)等不相关。现在吸烟 (风险比: 1.19; 95% CI: 1.08 ~ 1.32) 与总体VTE呈正相关,但主要观察到有诱因的VTE,可能是由包括癌症在内的合并症介导的。 然而,与VTE的经典危险因素 (吸烟风险增加1.3倍vs.癌症风险增加4 ~ 7倍) 相比,观察到的与吸烟相关的VTE风险(如果有的话)可以忽略不计。 值得注意的是,BMI可能低估老年人的整体身体脂肪含量,因为去脂体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使用腰围或腰臀比可以获得较好的体脂估计准确性。然而,目前尚无大型研究评估腰围或腰臀比在静脉和动脉血栓形成之间的混杂效应。 动脉和静脉疾病治疗 静脉和动脉血栓形成之间的重叠也增加了动脉心血管药物(特别是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对VTE的潜在有益或有害的可能性。 阿司匹林和抗凝剂: 阿司匹林是预防和治疗动脉疾病的基石药物。虽然与安慰剂相比,阿司匹林可有效预防全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术后的VTE,或最初6个月抗凝剂治疗后的VTE复发,但在VTE的二级预防方面,阿司匹林的效果低于全剂量或小剂量抗凝剂。 尽管如此,既往有卒中或心肌梗死病史且正在接受抗血小板药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发生VTE。在抗血小板药物的基础上加用抗凝剂将导致出血风险显著增加。最近的研究和指南越来越多地建议,在需要抗凝剂(用于VTE或心房颤动)的情况下,尽早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即使是近期置入药物洗脱支架的患者 (这是高风险的情况)。 在稳定型冠心病合并心房颤动患者中,日本最近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单独使用利伐沙班进行抗凝与利伐沙班+阿司匹林联合抗凝同样安全有效。虽然本试验尚未在其他人群中得到验证,但将这些数据扩展到稳定型冠心病合并VTE患者似乎是合理的:在VTE急性期或VTE长期治疗中,抗凝剂单药治疗将降低VTE复发和心肌梗死的风险。 然而,对于VTE的长时间抗凝治疗 (即超过前6个月的治疗) 仍需进一步研究,因为目前尚不清楚小剂量直接口服抗凝药(即阿哌沙班2.5 mg BID,利伐沙班10 mg OD)是否足以预防肾功能正常患者的动脉事件复发。对于同时需要抗血小板药物(如既往冠心病、冠状动脉支架)的心房颤动患者,也存在同样的观点。 相反,对于发生心肌梗死且有抗凝治疗适应证的患者,通常建议避免置入药物洗脱支架,以缩短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持续时间并降低出血风险。 此外,在冠心病和卒中患者中,持续抗凝治疗是全身性溶栓治疗的禁忌证。 他汀类药物和VTE: 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提示,使用他汀类药物与VTE风险降低相关,而与贝特类药物无关联或呈负相关。 由于他汀类和贝特类药物均对血脂有效,因此这些降脂药物如何改善VTE风险尚不清楚。两项荟萃分析评估了他汀类药物对VTE风险的潜在影响。 第一项荟萃分析包括8项病例对照研究、3项队列研究和JUPITER试验(约80万名受试者)。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VTE风险降低显著相关(OR: 0.81; 95% CI: 0.66 ~ 0.99)。 第二项荟萃分析包括6项病例对照研究、3项队列研究和JUPITER试验(约97万名受试者)。总体而言,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VTE发生风险的显著降低相关(OR: 0.68;95% CI: 0.54 ~ 0.86)、DVT (OR: 0.59; 95% CI: 0.43 ~ 0.82)和PE (OR: 0.70; 95% CI: 0.53 ~ 0.94)。 虽然JUPITER是唯一一项比较他汀类药物与安慰剂用于VTE一级预防的试验,但VTE的发生是多项次要研究结局之一。因此,应谨慎解读该试验。 6项观察性研究利用用药数据比较了他汀类药物用药者和非用药者的VTE复发率。来自丹麦(N = 44,330, N = 27,862)、加拿大(N = 25,681)、荷兰(N = 2547, N = 3093)和米国(N = 2798)的队列显示他汀类药物使用者的VTE复发率降低。 这一发现的例外是一个较小的法国队列,该队列对432例首次发生无诱因VTE的患者进行了前瞻性随访,并报告他汀类药物暴露与复发性VTE的减少不相关。 2017年,对8项观察性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发现,他汀类药物在VTE二级预防中具有保护作用(RRR为27%)。 SAVER试点研究(他汀类药物减少静脉血栓栓塞患者的静脉事件:一项初步研究评估了一项RCT的可行性,该RCT评估了仿制瑞舒伐他汀可否降低有症状的严重VTE患者的复发性VTE风险)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试点研究(NCT02679664),该研究成功地证明了在一项比较瑞舒伐他汀和安慰剂治疗症状性VTE患者的更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中招募患者的可行性。 国际静脉血栓形成网络将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共计2700例患者,目的是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即瑞舒伐他汀在标准/常规抗凝治疗VTE的基础上是否有临床相关益处。本研究获得了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 # PJT 166095)的资助。 总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对动脉和静脉血栓形成之间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动脉疾病的传统危险因素似乎与VTE风险增加并不强相关;然而,VTE患者携带这些危险因素,应在发生VTE时进行检查、重新评估,并加倍努力管理心血管危险因素。 他汀类药物是治疗VTE很有前景的药物。它们在VTE二级预防中的疗效将很快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进行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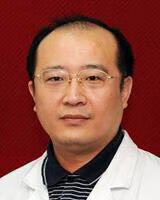
吕平
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52人阅读
查看详情
文章
2023年诺贝尔医学奖公布
Katalin Karikó和Drew Weissman因开发mRNA疫苗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2021年10月22日,周五,在西班牙北部奥维耶多的一个仪式上,Katalin Kariko与其他6名科学家一起,从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公主莱昂诺尔手中接过了2021年阿斯图里亚斯公主技术和科学研究奖。2023年10月2日(当地时间),诺贝尔医学奖被宣布授予使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开发成为可能的Katalin Karikó和Drew Weissman。 2名科学家因开发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有效mRNA疫苗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Katalin Karikó是匈牙利萨根大学的教授,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兼-职教授。Drew Weissman与Karik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完成了他的获奖研究。 诺贝尔大会秘书Thomas Perlmann周一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了这一奖项。 去年,瑞典科学家Svante Paabo因在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发现解开了尼安德特人DNA的秘密,为了解我们的免疫系统提供了关键见解,包括我们对严重COVID-19的脆弱性。 这是家族中第二次获奖。Paabo的父亲Sune Bergstrom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诺贝尔奖将于周二公布物理学奖,周三公布化学奖,周四公布文学奖。诺贝尔和平奖将于周五公布,经济学奖将于10月9日公布。 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100万刀[美元])。这笔钱来自该奖项的创造者、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留下的遗产。诺贝尔于1896年去世。 由于瑞典货币的暴跌,今年的奖金增加了100万克朗。 获奖者将被邀请在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的颁奖典礼上领奖。根据他的意愿,久负盛名的和平奖将在奥斯陆颁发,而另一个颁奖仪式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 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大会今天决定将20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共同授予: Katalin Karikó和Drew Weissman 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从而开发出了有效的COVID-19 mRNA疫苗。 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发现对于在2020年初开始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至关重要。这些开创性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mRNA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在现代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期间,这些获奖者为疫苗研发的空前速度做出了贡献。 大流行前的疫苗 接种疫苗刺激形成对特定病原体的免疫反应。这使身体在以后接触疾病的情况下,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以灭活或弱化病毒为基础的疫苗早已问世,例如脊灰、麻疹和黄热病疫苗。1951年,Max Theiler因开发黄热病疫苗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由于近几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基于单个病毒成分而不是整个病毒的疫苗已经被开发出来。病毒遗传密码的一部分,通常编码在病毒表面发现的蛋白质,被用来制造刺激病毒阻断抗体形成的蛋白质。例如针对乙型肝炎病毒和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或者,部分病毒遗传密码可以转移到无害的病毒载体,即“载体”。这种方法用于埃博拉病毒疫苗。当注射载体疫苗时,我们的细胞会产生选定的病毒蛋白,刺激针对目标病毒的免疫反应。 生产基于病毒、蛋白质和载体的全疫苗需要大规模的细胞培养。这一资源密集的过程限制了为应对疫情和大流行而快速生产疫苗的可能性。因此,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开发不依赖细胞培养的疫苗技术,但这被证明具有挑战性。 mRNA疫苗: 一个有希望的想法 在我们的细胞中,DNA编码的遗传信息被传递给信使RNA (mRNA),信使RNA被用作蛋白质生产的模板。20世纪80年代,人们提出了一种无需细胞培养即可产生mRNA的有效方法,称为体外转录。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加速了分子生物学在多个领域应用的发展。将mRNA技术用于疫苗和治疗的想法也开始了,但前面还存在障碍。体外转录的mRNA被认为不稳定,难以递送,因此需要开发复杂的载体脂质系统来封装mRNA。此外,体外产生的mRNA可引起炎症反应。因此,开发用于临床目的的mRNA技术的热情最初受到限制。 这些障碍并没有阻止匈牙利生物化学家Katalin Karikó,她致力于开发利用mRNA进行治疗的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她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助理教授时,尽管在说服研究资助者她的项目的重要性方面遇到了困难,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愿景,即实现mRNA作为一种疗法。Karikó的一位新同事是免疫学家Drew Weissman。他对树突状细胞感兴趣,树突状细胞在免疫监视和疫苗诱导的免疫应答激活中具有重要功能。在新想法的刺激下,两人很快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重点是不同的RNA类型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 突破 Karikó和Weissman注意到,树突状细胞将体外转录的mRNA识别为一种外来物质,这导致了它们的激活和炎症信号分子的释放。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体外转录的mRNA被识别为外源mRNA,而来自哺乳动物细胞的mRNA却没有引起同样的反应。Karikó和Weissman意识到一些关键特性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mRNA。 RNA包含4个碱基,缩写为A、U、G和C,分别对应DNA中的A、T、G和C,这是遗传密码的字母。Karikó和Weissman知道,来自哺乳动物细胞的RNA中的碱基经常被化学修饰,而体外转录的mRNA则没有。他们想知道,在体外转录的RNA中,没有改变的碱基是否可以解释不必要的炎症反应。为了研究这一点,他们产生了不同的mRNA变体,每个变体的碱基都有独特的化学变化,并将其递送给树突状细胞。结果是惊人的:当碱基修饰包含在mRNA中时,炎症反应几乎被消除。这对我们理解细胞如何识别和响应不同形式的mRNA是一个范式的改变。Karikó和Weissman立即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对使用mRNA进行治疗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开创性结果发表于2005年,也就是COVID-19大流行发生的15年前。 在2008年和2010年发表的进一步研究中,Karikó和Weissman表明,与未修饰的mRNA相比,通过碱基修饰产生的mRNA的递送显著增加了蛋白质的生成。这种效应是由于调节蛋白质生成的一种酶的激活减少。Karikó和Weissman发现碱基修饰既能减少炎症反应又能增加蛋白质的生成,他们消除了mRNA临床应用的关键障碍。 mRNA疫苗实现了它们的潜力 人们开始对mRNA技术产生兴趣,2010年,几家公司开始致力于开发这种方法。研发寨卡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疫苗;后者与SARS-CoV-2密切相关。COVID-19疫情暴发后,编码SARS-CoV-2表面蛋白的两种碱基修饰mRNA疫苗以创纪录的速度被开发出来。据报告,保护效果约为95%,两种疫苗最早于2020年12月获得批准。 mRNA疫苗的开发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灵活性和速度,这为将新平台也用于预防其他传染病的疫苗铺平了道路。在未来,该技术还可能被用于递送治疗性蛋白质和治疗某些癌症类型。 基于不同方法的其他几种SARS-CoV-2疫苗也迅速推出,全球共接种了130多亿剂COVID-19疫苗。这些疫苗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防止了更多人患上严重疾病,使社会得以开放并恢复正常状况。通过对mRNA碱基修饰重要性的基本发现,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健康危机之一期间对这一变革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出版物 Karikó, K., Buckstein, M., Ni, H. and Weissman, D. Suppression of RNA Recognition by Toll-like Receptors: The impact of nucleoside modif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RNA. Immunity 23, 165–175 (2005). Karikó, K., Muramatsu, H., Welsh, F.A., Ludwig, J., Kato, H., Akira, S. and Weissman, D. Incorporation of pseudouridine into mRNA yields superior nonimmunogenic vector with increased translational capacity and biological stability. Mol Ther 16, 1833–1840 (2008). Anderson, B.R., Muramatsu, H., Nallagatla, S.R., Bevilacqua, P.C., Sansing, L.H., Weissman, D. and Karikó, K. Incorporation of pseudouridine into mRNA enhances translation by diminishing PKR activation. Nucleic Acids Res. 38, 5884–5892 (2010). Katalin Karikó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Szolnok。1982年,她在赛格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赛格德的匈牙利科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直到1985年。随后,她在费城天普大学和贝塞斯达健康科学大学进行了博士后研究。1989年,她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助理教授,并一直任职到2013年。之后,她成为BioNTech RNA Pharmaceuticals的副总裁和高级副总裁。自2021年以来,她一直是赛格德大学(Szeged University)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兼-职教授。 Drew Weissman1959年出生于米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他于1987年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医学院的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学中心接受临床培训,并在米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7年,韦斯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成立了他的研究小组。他是罗伯茨家族疫苗研究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RNA创新研究所主任。 附:最近十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以下是过去10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名-单: 2022年: 瑞典古遗传学家Svante Paabo发现了灭绝的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 2021年: 米国搭档大David Julius和Ardem Patapoutian发现了人类感知温度和触觉的受体。 2020年: 米国人Harvey Alter和Charles Rice与英国人Michael Houghton共同发现了丙型肝炎病毒,导致了敏感的血液检测和抗病毒药物的开发。 2019年: 米国的William Kaelin和Gregg Semenza以及英国的Peter Ratcliffe为我们理解细胞如何反应和适应不同氧气水平奠定了基础。 2018年: 米国免疫学家James Allison和日本免疫学家Tasuku Honjo,他们发现了如何释放免疫系统的刹车,使其更有效地攻击癌细胞。 2017年: 米国遗传学家Jeffrey Hall, Michael Rosbash和Michael Young在控制大多数生物觉醒-睡眠周期的体内生物钟方面的发现。 2016年: 日本的Yoshinori Ohsumi,因其在自噬(细胞“吃掉自己”的过程)方面的研究而获奖。自噬被破坏会导致帕金森病和糖尿病。 2015年: William Campbell,爱尔兰出生的米国公民,日本的Satoshi Omura和中国的屠呦呦,因为他们解开了疟疾和蛔虫的治疗方法。 2014年: 米国出生的英国人John O'Keefe、Edvard I. Moser 和挪威的May-Britt Moser发现了大脑是如何通过“内在GPS”导航的。 2013年: 出生在德国的米国公民Thomas C. Sudhof,以及米国的James E. Rothman和Randy W. Schekman,研究细胞如何组织其运输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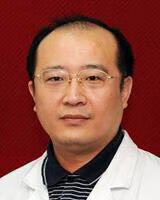
吕平
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24人阅读
查看详情
文章
氟喹诺酮类药物能否增加主动脉瘤或夹层风险
氟喹诺酮类药物是否会增加主动脉瘤或夹层的风险 一项使用两个数据库以及队列和交叉设计的观察性研究提示,之前报告的氟喹诺酮类药物用药与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风险之间的关联可能是由于混杂因素。 安全担忧和研究结果 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安全担忧导致米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在 2018 年发出警告,某些患者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会增加患主动脉瘤或夹层的风险。此外,之前的研究在关联的因果关系方面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 研究设计和结果 英国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硕士 Jeremy P. Brown 及其同事指出: 他们使用了多种研究设计来调查这些关联,并“增加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该研究在线发表在《JAMA Cardiology》杂志上,在考虑了潜在混杂因素或将氟喹诺酮类药物与其他抗生素进行比较后,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混杂因素和结论 研究者将临床实践研究数据链(Clinic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link ) Aurum 和 GOLD 初级保健记录与医院入院数据建立关联,从而开展队列研究和交叉研究。 队列研究纳入了 1997—2019 年全身性服用氟喹诺酮类或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成人。该研究团队估计了氟喹诺酮类药物与头孢菌素类药物相比,与处方开具后 60 天内因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之间的关联。成人马方综合征患者被排除。 在病例交叉研究中,首次因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的成人患者被纳入,并在年龄、性别、索引日期和临床实践方面以 1∶3 的比例匹配对照个体。 研究评估了在发生结局之前 60 日内,处方氟喹诺酮类药物与主动脉瘤或夹层之间的关联(与未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相比),以及与对照抗生素头孢菌素、复方阿莫昔拉夫和甲氧苄啶之间的关联。 在队列研究中,奥鲁姆(Aurum)3,134,121 名成人(平均年龄,52.5 岁; GOLD 组 452,086 例(平均年龄,53.9 岁; 63.4%的女性)被开出氟喹诺酮类或头孢菌素类药物。 在粗分析中,与头孢菌素相比,氟喹诺酮类药物与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增加相关(合并风险比[HR], 1.28 )。然而,在对潜在混杂因素进行校正后,上述关联消失(合并校正 HR, 1.03 )。 在病例交叉研究中,84,841 人因首次主动脉瘤或夹层在 Aurum 住院(平均年龄,75.5 岁; GOLD 组 10,357 例(平均年龄 75.6 岁; 27.1%的女性)。 与未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相比,处方氟喹诺酮类药物与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呈正相关(合并比值比,1.58 )。然而,比较抗生素的风险也升高,并且与比较抗生素相比,没有证据表明与氟喹诺酮类药物相关。 作者写道: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氟喹诺酮类药物与主动脉瘤或夹层的关联估计可能受到混杂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到这些混杂因素时,未发现明显关联,这使我们对氟喹诺酮类药物在主动脉瘤或夹层方面的安全性感到放心。 谨慎解读 纽约市西奈山卫生系统主动脉外科主任、医学博士 Ismail El-Hamamsy 在发表评论时表示: 应该谨慎解读这些发现。例如,马凡综合征患者或与主动脉瘤相关的遗传疾病患者,可能是最脆弱的人群,被排除在这项研究之外。 我们关注的结果是主动脉瘤或夹层。夹层是一种急性事件,与单一事件(前两个月的抗生素处方)之间的联系更容易确定。相反,在 60 天内诊断出动脉瘤并不能说明它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 基础感染可能只是导致影像学检查和意外诊断。因此,缺乏对动脉瘤和夹层的区分是本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性。 该研究并未说明氟喹诺酮类药物对已知主动脉瘤或结缔组织疾病患者的影响,而这正是 FDA 发出警告的原因。这些患者有较高的主动脉夹层或破裂风险。因此,对于这些患者,不应根据本研究考虑改变临床实践。 附 1:原文概要 在非干涉性研究中,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使用与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增加相关,但观察到这种关联的原因尚不清楚。 采用多个研究设计和多个数据库来确定氟喹诺酮类药物与主动脉瘤或夹层的关系,以增加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设计、设置和参与者队列研究和病例交叉研究分别在英国初级保健记录的两个数据库中进行。临床实践研究数据链 Aurum 和 GOLD 初级保健记录与医院入院数据相关联。队列研究纳入了 1997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全身性服用氟喹诺酮类或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成人。病例交叉研究纳入符合条件的成人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患者。病例交叉研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个体在年龄、性别、索引日期和临床实践方面进行 1: 3 匹配以对照个体,以调整处方的日历趋势。数据分析时间为 2022 年 1 月至 7 月。 暴露: 全身性氟喹诺酮类或比较抗生素。 在队列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治疗加权的稳定逆概率 Cox 回归,估计了处方氟喹诺酮类药物与因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之间的关联的风险比(HRs )。在病例交叉研究中,采用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评估全身氟喹诺酮类药物使用与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之间的关联的比值比(OR )。利用固定效应荟萃分析将各数据库的估计值合并。 在队列研究中,研究团队在 Aurum 确定了 3134121 名成人,在 GOLD 确定了 452 086 名成人,医师开出了氟喹诺酮类或头孢菌素类药物。在粗分析中,相对于头孢菌素的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与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增加相关,但针对潜在混杂因素进行校正后,这一关联消失。在病例交叉研究中,研究团队确定了 84 841 例因主动脉瘤或夹层在 Aurum 住院的患者和 10 357 例在 GOLD 住院的患者。与不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相比,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与主动脉瘤或夹层住院增加相关,但未发现与其他抗生素相关(TIPS: 具体统计数据被略去)。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氟喹诺酮类药物与主动脉瘤或夹层的关联估计可能受到混杂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到这些混杂因素时,未发现明显关联,这使我们对氟喹诺酮类药物在主动脉瘤或夹层方面的安全性感到放心。 附 2:氟喹诺酮类药物 1979 年合成第一个代喹诺酮药:诺氟沙星(Norfloxacin 氟哌酸)。它是 4-Quinolone 结构改造衍生物,在 6 位上加上一个氟(F )后,增加了脂溶性,增强了对组织细胞的穿透力,因而吸收好,组织浓度高,半衰期长,更大大增加了抗菌谱和杀菌效果。此后,构效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展开,近年来新的氟喹诺酮类药物如雨后春笋,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氟喹诺酮类对 G-杆菌,包括绿脓杆菌均有良好抗菌作用,对 G+球菌也具一定抗菌活性,尤其对耐药 G-杆菌,仍可呈现敏感。 氟喹诺酮类药物具有以下特点 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尤其对 G-杆菌的抗菌活性高,包括对许多耐药菌株如 MRSA(耐甲氧西林金葡菌)具有良好抗菌作用; 耐药发生率低,无质粒介导的耐药性发生; 体内分布广,组织浓度高,可达有效抑菌或杀菌浓度; 大多数系口服制剂,亦有注射剂,半衰期较长,用药次数少,使用方便; 为全化学合成药,价格比疗效相当的抗生素低廉,性能稳定,不良反应较少。 氟喹诺酮类药物临床应用 临床用于治疗尿路、肠道、呼吸道以及皮肤软组织、腹腔、骨关节等感染,取得良好疗效,不良反应轻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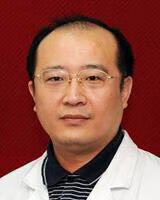
吕平
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22人阅读
查看详情
文章
共生共享循环系统延缓细胞衰老 延长寿命达10%
共生共享循环系统延缓细胞衰老 延长寿命达10% 这项研究由米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 杜克健康(Duke Health)的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外科手术将年轻和年老小鼠的循环系统连接起来,这一过程被称为"异时异种共生" (heterochronic parabiosis) ,可以减缓细胞衰老,并将年老小鼠的寿命延长至多10%。小鼠共享血液循环的时间越长,其抗衰老作用越持久,揭示了年轻血液成分具有年轻化、改善生理能力、延长寿命的潜力。 米国杜克大学与杜克医学中心 动物共享循环系统的时间越长,对老年小鼠的益处就越持久。 研究发现,通过手术将年轻和年老的老鼠的循环系统连接起来,可以在细胞水平上减缓衰老,并将年老动物的寿命延长10%。 最近发表在《自然·衰老》(Nature Aging)杂志上的一项由杜克健康研究人员领导的研究发现,动物共享血液循环的时间越长,一旦两者不再联系,抗衰老的益处持续的时间就越长。 研究结果表明,年轻人从他们血液中有助于保持活力的成分和化学物质的混合物中获益,这些因素有可能被分离出来,作为加速愈合、恢复身体活力和延长老年人寿命的疗法。 资深作者James White博士是杜克大学医学院和杜克衰老中心医学和细胞生物学部门的助理教授。 研究者指出: 这是第一个证明这个被称为异时异种共生的过程可以减缓衰老的速度,这伴随着寿命和健康的延长。 White和同事们开始研究异时异种共生(通过手术将不同年龄的两只动物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共享的循环系统)的益处是短暂的,还是更持久的。 杜克大学(Duke)和其他地方的早期研究证明,在三周的异种共生后,老龄小鼠的组织和细胞具有抗衰老的益处。这些研究发现,年老的老鼠变得更活跃,它们的组织显示出年轻化的证据。 研究者指出: 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在三周的异种共生中看到这些抗衰老的效果,如果你把它延长到12周,会发生什么呢?这大约是老鼠3年寿命的10%。 老鼠的年龄也很重要,小老鼠4个月大,大老鼠2岁。 经过两个月的随访,老年动物的生理能力有所提高,比未接受手术的动物寿命延长10%。 在细胞水平,异种共生显著降低了血液和肝组织的表观遗传年龄,并显示出与衰老相反的基因表达变化,但类似于限制热量等几种延长寿命的干预措施。 即使在脱离两个月后,年轻化的效果仍然存在。 就人类而言,这种异种共生的影响相当于让一个50岁的人与一个18岁的人配对约8年,这种影响会使人的寿命增加8年。 研究者指出: 这项实验旨在研究长期接触年轻老鼠的血液是否会对老年老鼠产生持久的影响。 为异时异种共生配对人类显然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其他的抗衰老策略,如热量限制,可以更好地延长小鼠的寿命。 我们的工作表明,有必要探索年轻血液循环中的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抗衰老现象。我们已经证明,这种共享循环可以延长老年小鼠的生命和健康,接触的时间越长,变化越持久。 推动这一变化的因素是重要的,但它们还不为人所知。它们是蛋白质还是代谢物?是年轻的老鼠提供了新的细胞,还是年轻的老鼠只是缓冲了衰老的血液?这是我们接下来希望了解的。 论文:Multi-omic rejuvenation and lifespan extension on exposure to youthful circulation. Bohan Zhang, David E. Lee, Alexandre Trapp, Alexander Tyshkovskiy, Ake T. Lu, Akshay Bareja, Csaba Kerepesi, Lauren K. McKay, Anastasia V. Shindyapina, Sergey E. Dmitriev, Gurpreet S. Baht, Steve Horvath, Vadim N. Gladyshev and James P. White, 27 July 2023, Nature Aging. DOI: 10.1038/s43587-023-00451-9 另附:来自米国另一所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衰老与代谢生物学研究所(明尼阿波利斯)提供的相关信息 啮齿类动物衰老模型是研究衰老和年轻化机制的重要工具。然而,在啮齿类动物模型中,很难区分衰老的细胞自主和细胞非自主方面。异种共生是研究两个手术配对动物之间共享的循环因子的细胞非自主效应的宝贵方法。 这项技术是由保罗·伯特(Paul Bert)在19世纪60年代首创的,并一直沿用至今。在衰老领域特别有趣的是异时异种共生(heterochronic parabiosis, HP)的使用,即年轻和年老的小鼠配对在一起形成共享的血液供应。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HP已经证明暴露于年轻小鼠的循环环境可以使老年小鼠的许多生物过程恢复活力,包括骨再生、肝发生、肌肉发生和神经发生。有趣的是,在一些报告中,这些特征在机制上与特定的血源性蛋白质(称为抗老年性因子)以及推测的相关通路相关。 相反,HP也被用于鉴定在老年小鼠中发现的促衰老因子,这些因子能够驱动年轻异时性伴侣的衰老。HP领域的这些开创性发现促使一些公司成立,这些公司要么销售“年轻血液”,要么测试年轻血浆或富集血浆组分输注对年龄相关慢性疾病的疗效。因此,HP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来分别评估年轻和老年环境对衰老特征的影响。 衰老的一个标志是细胞衰老,这是一种由外部和内部细胞应激信号引起的细胞命运,通过包括p16INK4a/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和/或p53/p21CIP1在内的转录因子级联反应建立,导致基因表达、组蛋白修饰、细胞器功能、蛋白质生成增加以及深刻的形态和代谢改变的广泛变化。 相当一部分衰老细胞释放炎症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蛋白酶、生物活性脂质、前体素、细胞外囊泡和促凝血因子,这些被称为衰老相关分泌表型或SASP,目前推测SASP可驱动体内外周或继发性衰老。 在明尼苏达大学这个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中,他们使用HP来研究细胞非自主性对小鼠衰老细胞负荷的影响。在6或20月龄小鼠的多个组织中测定了细胞衰老标志物和SASP因子,这些小鼠等时或异时配对2个月。 与年轻的同时共生(YY)小鼠相比,经典的衰老标记物p16Ink4a和p21Cip1在老年同时配对(OO)小鼠的部分组织(前脑,肾,肝,肺和胰腺)中表达显著升高。与老年同时配对(OO)小鼠相比,老年异时共生(OY)小鼠组织中p16Ink4a和p21Cip1表达降低。 令人惊讶的是,与同时对照(YY)相比,p16Ink4a和p21Cip1在年轻异时共生(YO)组织中的表达同时增加。在相同的组织中,研究者观察到类似的模式表达的SASP因子(il1 β, Il6, Mcp1和Tnfa)。MCP-1是一种负责单核细胞募集的趋化因子,也是生物衰老的替代生物标志物,他们定量检测了HP小鼠肾脏和肝脏中MCP-1的蛋白水平。 与相应对照组(YY/OO)相比,MCP-1蛋白在老年异时共生体(OY)中表达降低,在年轻异时共生(YO)中表达升高。这些衰老的变化被一些组织的复合病变评分所证实,该评分基于使用老年病理分级平台对年龄相关的组织病理学病变进行的评估。 这些发现清楚地表明,细胞衰老可能受到系统环境的影响,HP所观察到的年轻化效应可能是通过减少衰老细胞负荷来介导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年轻共生体的循环功能性T或NK细胞也可能通过清除老年伴侣的衰老细胞来减少衰老细胞负荷。 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最近提出的饱和去除(SR)模型一致,在SR模型中,衰老细胞的累积产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线性增加,衰老细胞抑制其自身的去除。未来,应用新兴的单细胞和空间基因组学方法来更好地检测和表征衰老细胞,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细胞随年龄增长而非自主调节衰老细胞负荷的机制。 对来自HP小鼠的细胞和组织进行的最初多组学分析显示,老年异时性共生体的转录组和表观遗传时钟发生有益变化,这提示暴露于年轻因素足以使生物钟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此外,这些积极作用在老年HP小鼠中持续到分离后两个月。 未来的实验可能包括使用HP亲代中p16INK4a+和p21CIP1+衰老细胞的遗传模型,以研究衰老细胞在驱动年轻小鼠衰老细胞增加和组织稳态丧失中的作用。综上所述,这种通过HP研究循环因子在细胞和组织年轻化中的作用的方法仍然是有意义的,并且可以用于解决衰老中的许多关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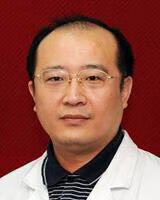
吕平
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43人阅读
查看详情